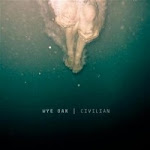剛抵達倫敦宿舍的那個晚上,
有個黑人女孩向我問最近的地鐵站在哪,
我搖頭對她說我不知道,
她用夾著責怪與不可置信的表情看了我一眼快步離開。
大約十分鐘後我才發現,
離她問我路的街道走路三分鐘內就有個地鐵站,
而她正拖著行李大步往反方向走。
住我隔壁房的是一個嬌小,來自香港的女孩,
叫做潔熙,在中央聖馬丁上通識基礎課程,
她是不折不扣的白人,父親是英國人,母親是保加利亞人,
從小在香港長大,在英語學校讀書,
她所熟悉的英國還有保加利亞,是每年渡假探親時的體驗,
對她而言香港才是家鄉,但中文與廣東話學了十年,
她仍無法使用,甚至寫不好一個中文字。
她說以前在香港校內,白人與東方人在教室內彼此隔離,
互不往來,無論是作業分組或交朋友,似乎都有各自的世界。
她自己倒是有幾個港人朋友,也交了一個現居香港的韓國男友。
我到的第二天她跑來敲門打招呼,
聊了幾句她反而詞窮而尷尬著。
幾天後,一個在中央聖馬丁學院
讀藝術評論的瘦高大鬍子在宿舍辦了個派對,
潔熙拉著我跟另一房的英國女孩衝上樓到他們寢室的廚房。
瘦高大鬍子手上總拿著個高腳杯,穿著又緊又憋的黑色牛仔褲,
上身隨便套著寬鬆的白T,
跟人聊了幾句便走去開冰箱把自己杯子裡添滿白酒,
再晃啊晃的跟其他到來的人擁抱,左臉右臉互碰親空氣。
來參與的人很少,我們意興闌珊的玩著牌,
他則跑進跑出的去找人來。
音樂放得太大聲,用的是很差的迷你音箱,
尖銳的交替放著濫製的舞曲與搖滾樂,
刺耳的聽不清大家說話的聲音。
我們問著彼此上些什麼課目,為什麼選擇這課目。
問到大鬍子,為什麼選擇藝術評論?為什麼想當藝評?
他有些不耐而高傲的說:「因為我不想漠視。」
我不喜歡這樣的答案,像是為自己找了個冠冕堂皇的理由,
心裡仍是困惑的,不得其解卻輕易結論。
然而我看待評論家或史學家總不太客觀,
更別說是一個剛上大學,自視甚高的評論家。
偉大畫家與建築師打造的是未來,評論家與史學家僅留在過去,卻用過去批判未來。
另一個同在中央聖馬丁學院的女孩說她讀的是織品設計,
她說她愛時尚,但對衣服樣式沒什麼興趣,
想做的是打造好看的布料樣式。
我問她我們這間大學究竟在英國評價如何,
她侃然談著,並一一說著各學院的差異,
有些學院強在雕塑、平面藝術,有些學院是傳播名校,
我的學院是裝置藝術,而他們的當然是時裝。
她說聖馬丁和我的學院彼此憎惡,我好奇問著原因,
她說因為兩個學院都跟藝術與時尚相關,卻又有些差異,
所以彼此競爭等等的。
理由總說不太清,我笑著心想那挺像孩提時的把戲,
總要分成好幾派彼此競爭,視為仇敵,真的出社會,老在競爭中渡過便總質疑著這一切有何意義。
進駐宿舍的第一週,我沒遇過台灣人,也少見黃種人。
我上了宿舍臉書頁面貼文,尋找同住在此的亞洲人,僅有一個人回應,他來自台灣,名叫威廉。
當天晚上他打了通電話和我約在他寢室區的共用廚房,
餐桌四個座位都坐滿了人,
他托旁邊一位金髮男孩從房間拿了把椅子給我。
我坐了下來,左手邊是一個不多話,
鼻環龐克路線的女孩,名叫奧利薇亞,
右手邊坐的是拿椅子給我的金髮男孩,叫傑米,
對面坐著威廉和一個戴著黑框眼鏡,
瀏海綁馬尾的深黑髮色英國女孩,名叫露西。
我仍不習慣跟滿室外國人用英文應答,
那台灣男孩卻顯得自然的很。
他和露西正在大口吃著晚餐,
他們顯然不黯廚藝,威廉煮了義大利螺絲麵,
攪上罐裝麵醬,丟進火腿,滿滿一鍋足以餵飽一家四口。
露西則是速煮冷凍調理包千層麵。
威廉在台灣新竹出生,媽媽是台灣人,
繼父是蘇格蘭人,我笑說難怪他的姓氏不是中國的。
他說自己幾乎一輩子都在海外度過,
待過美國洛杉磯、荷蘭愛荷芬,現在到了英國倫敦,
讀的是媒體與文化學。
他興奮的說沒想到能在同宿舍找到一樣來自台灣的人,
這麼多年在外國生活,國語都說不順口了。
他跟傑米挺要好,聊著一些他們的共同朋友跟共同知道的事,
他說傑米還有一項絕招:聽中文歌。
我說以前在台灣我在做電台主持,音樂性的節目,
威廉推著他講幾個他聽的華人歌手,
他紅著臉說在專業的人面前講丟臉的很,
我也推著他快說,好奇到底聽過哪些歌。
傑米講了幾個歌手名字,王菲周杰倫等等,
我挺驚訝在這裡
居然有個剛上大學的英國男孩對東方流行文化有興趣。
飯飽後聊了一下子,三個英國室友想外出找個酒吧廝混先行離去了。
我和威廉對夜生活沒那麼感興趣,留下來聊了一陣,
他說畢業後想回台灣工作,想好好的住在台灣一段時間,
我說台灣媒體業賺的不多,也不太在乎學歷。
他有些遲疑,說等三年後畢業再想想去處吧,
我說若他真想回台灣,我可以替他介紹地方工作,
他興奮的笑著,說話音調也提高了。
幾天後他在我的臉書版面上留言,要問我怎麼煮中式蔬菜,
我說我的電鍋也寄到了,
不如找一天到中國城買些食材辦個亞洲派對吧。
他迫切找回自己的台灣根源,有個愛聽中文歌的英國朋友,
還想嚐嚐道地的中國菜。隔了兩天我興緻一來,拉了他去中國城,
買了三大袋的食材,抓了隔壁房潔熙一起來吃飯,
四菜一湯,一大盤塔香沙茶牛肉,一盤煎沙嗲豆腐,
另兩盤是炒波菜跟青江菜,跟一鍋味增湯,道地台式口味。
潔熙不吃肉,只碰素菜。
三人吃的津津有味,話也不聊了,
拼了命扒飯夾菜,桌面一掃而空。
我大半輩子也總在海外度過,巴黎、溫哥華,現在到了倫敦。
我說不上自己該屬於哪種文化,在台灣我總顯得洋味,
到了外國卻不折不扣覺得自己真是東方的很。
潔熙說自己每到週末就回去英國的爺爺奶奶家,
衣服可以拿去那裏洗,有大餐,回來還可以帶些食材省錢,她笑說有爺爺奶奶真好。
她17歲,正找回自己的英國根源。
我想自己的台灣根源應該是幼年時跟爺爺奶奶同住時打下的,
十幾年在國外有些忘了,這些年在台灣工作又找回。
我卻厭惡著那些文化標籤,
好像因為是那個國家那個文化就非得會有某些表現某些態度等等。
於是我們被膚色困住,被語言困住,被國籍困住,
然後被合理或不合理化我們一切的行為舉止,
然後如同羊群被趕入同一個圈子裡。
我總是想掙脫。
倫敦是個文化匯集地,
據說真正的倫敦本地人不多,大多都是外來者。
雖是匯集了,文化從未融合,壁壘分明的劃清地盤,
偶爾邀請你來做客,有時在你面前開一槍。
你總是不屬於任何一塊,除了有時猛然想起,
碰碰自個身體,確認自己總仍存在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