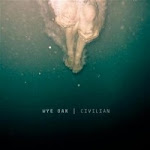自從地震及洪水摧毀了城市的信仰中心後,
這裡儼然成了聖書上記載的薩瑪惡城。
他們掠奪經途的旅人,
在俘虜胸口上烙下跟他們身上相同的印記,
再依照年齡、種姓、階級、樣貌,
一一分發到城內各層級。
城內層級是原先留下的,
淨白袍、單徽白袍、雙徽白袍...
以及庶民們穿的染白袍,混雜著其他顏色。
各級徽章細分下還有不同層級,
唯有淨白袍,用著最細緻的白絲紡成,
不得沾染任何烏塵。
昔日,聖堂是由淨白袍長老們所掌管,
終日燒燃著最高級的乳香、安息香、檀香,
全是原自北方高地。
早晨與夜間水鐘響過後,是全城最安靜的時刻。
他們將此稱之為「淨靈」,
所有人把思緒淨空,忘卻一切不美好、不愉快的事物,
再安然入眠,或面對新的一日。
地震後,聖堂崩塌的那一刻,全城陷入了恐慌,
一種靜默無聲的恐慌。
人們仍舊依照著往日的方式生活,
試圖在同一個時間淨靈,
但少了水鐘的提醒,於是城內開始失序。
當先失序的是淨白袍長老們,
聖堂崩塌後,他們試圖重建,
卻發現聖堂內的每一塊石磚、石板,
都是以大小、形狀不一的幾何圖形拼湊而成。
每個石磚、石板都有其神聖意涵,
並且拼接著不同的聖文記載。
長老們試圖將每一塊石磚、石板拼湊回原貌,
在這浩大工程進行的初期,暴雨與洪水接著出現,
將神聖的石磚、石板沖到了下游,遠至艾索拉荒城。
長老們南下找尋石磚、石板,帶回來的並非沉重的聖石,
而是在艾索拉流浪的少年與少女們。
最新消息:
我在倫敦,我很好,勿念。
2009年11月15日 星期日
2009年11月1日 星期日
Goodbye
老人在翻找著垃圾桶,就在我前往畫室的路上。
我仍穿著輕薄的短袖夏季服飾,燥熱難耐,
還等待著冷氣團到來,結束一切夏天的狂熱。
那天有人問起了 How did you fell?
才再次仔細的回想了所有過程,
我說,因為這一切的場景太美好了。
我們在颱風天吃完可口的披薩,
在停了電的陽明山上,
恰巧的坐在漢堡店的兩盞緊急照明燈下喝著熱茶談天。
這個夏天有看不完的演唱會,
那些目眩神迷的、懷舊、新奇的...
幾乎每個星期,都有一次令人愉悅的演唱會。
我們瘋狂的到基隆,吃了夜市小吃,
再從大風中,雨霧瀰漫的北海岸中緩慢開車回家,
像是經歷一場冒險。
甚至僅是開車經過高架橋時,忽然橋邊放起了慶賀的煙火...
"Maybe you're meant to find each other."
那些時刻,我的確是這麼認為的。
倘若不是一場上天安排的畫面,
又怎麼會一而再的出現諸多巧合?
而那些美好的,又從何時轉成苦澀?
我想...就在那一場慌亂,作勢欲嘔的不知所措之後吧。
當時,我很明白自此之後的每一步都會感到煎熬,
但我仍走了下去,
只希望能延續最初的美好,
並且相信過了黑夜,終究會天亮。
總覺得自己是不擅表達的人,
而唯一能表現的方式,是盡力的對一個人付出。
後來我懂了,
原來付出是不具意義並且滿是壓力的,不是嗎?
我總是記得每個大小的美好或苦澀畫面,
從好久好久以前的事情,
小時候到現在,都像是電影一樣的播放著。
我想,我會記得這一次的畫面。
我還記得在陽明山與北海岸之後的隔日早晨醒來,
仍在一場恍惚中,
盥洗後我躺回床上發呆,心不斷跳動著。
我難以呼吸,總想著這是什麼感覺...
耳邊忽然聽到一句話,開頭喊著"綿羊..."
但心中還帶著數個月前的傷,忽然對這一切感到害怕...
害怕...卻很快樂。
而後當每一次感到苦澀時,最初的感動總支撐著我,
只想如此堅持,並延續著。
在法國的旅程中不斷回想,
某天忽然驚覺,我總是說那些場景太美好,
卻忘了一場關係應當在乎著對方對你有多好。
我們始終是兩個駕著車的人,
總看著前方播映的,
卻沒有多花點時間看著彼此最耀眼的部分,
也沒有專心在乎彼此真正想要的是什麼。
朋友說中了,maybe we're meant to find each other.
因為我在這場夏季的狂熱中,
不斷的看到Deja vu,
老師說,那就是你生命中必然會發生的事情,
才會在無意識中已然看過。
我看著那個拾荒老人,心中忽然一片酸楚。
那晚,在陽明山的緊急燈光下,
其實我想說,
最初見面的那一刻,其實我們都對彼此嫌惡著,
你對於片肉不沾的我感到惱人,
我也對於那張撲克臉跟一副愛理不理的態度感到討厭,
倘若不是拾荒老人,
不是那包菸跟那罐茶的瘋狂,
我不會想再次共享一頓晚餐,也許我們就擦身而過。
而在那場作勢欲嘔的慌亂後隔天,
冷氣團終於到了,
我想拋開一切狂熱,
回到最原本,簡約的生活。
沒有一大群朋友的熱絡,
但圍繞在我身邊的人,
卻總是能找來放心的聊些最深刻的心事。
我只想靜靜的當個書蟲,
在畫室不斷的畫畫,在剩餘有限的時間中向目標邁進,
我等待著一個能延續友情的apology,
卻遲遲未到。
才發現原來這麼簡單的一句話,
也必須如此漫長的等待。
我如此掙扎著是否按下刪除鍵,
即使明白按下了也不見得能回到原來的生活,
但至少,不能再讓心牽動。
如果我們真的有著最初的特殊緣分,
一定會再相遇的,不是嗎。
Goodbye then my dear friend...
Goodbye.
我仍穿著輕薄的短袖夏季服飾,燥熱難耐,
還等待著冷氣團到來,結束一切夏天的狂熱。
那天有人問起了 How did you fell?
才再次仔細的回想了所有過程,
我說,因為這一切的場景太美好了。
我們在颱風天吃完可口的披薩,
在停了電的陽明山上,
恰巧的坐在漢堡店的兩盞緊急照明燈下喝著熱茶談天。
這個夏天有看不完的演唱會,
那些目眩神迷的、懷舊、新奇的...
幾乎每個星期,都有一次令人愉悅的演唱會。
我們瘋狂的到基隆,吃了夜市小吃,
再從大風中,雨霧瀰漫的北海岸中緩慢開車回家,
像是經歷一場冒險。
甚至僅是開車經過高架橋時,忽然橋邊放起了慶賀的煙火...
"Maybe you're meant to find each other."
那些時刻,我的確是這麼認為的。
倘若不是一場上天安排的畫面,
又怎麼會一而再的出現諸多巧合?
而那些美好的,又從何時轉成苦澀?
我想...就在那一場慌亂,作勢欲嘔的不知所措之後吧。
當時,我很明白自此之後的每一步都會感到煎熬,
但我仍走了下去,
只希望能延續最初的美好,
並且相信過了黑夜,終究會天亮。
總覺得自己是不擅表達的人,
而唯一能表現的方式,是盡力的對一個人付出。
後來我懂了,
原來付出是不具意義並且滿是壓力的,不是嗎?
我總是記得每個大小的美好或苦澀畫面,
從好久好久以前的事情,
小時候到現在,都像是電影一樣的播放著。
我想,我會記得這一次的畫面。
我還記得在陽明山與北海岸之後的隔日早晨醒來,
仍在一場恍惚中,
盥洗後我躺回床上發呆,心不斷跳動著。
我難以呼吸,總想著這是什麼感覺...
耳邊忽然聽到一句話,開頭喊著"綿羊..."
但心中還帶著數個月前的傷,忽然對這一切感到害怕...
害怕...卻很快樂。
而後當每一次感到苦澀時,最初的感動總支撐著我,
只想如此堅持,並延續著。
在法國的旅程中不斷回想,
某天忽然驚覺,我總是說那些場景太美好,
卻忘了一場關係應當在乎著對方對你有多好。
我們始終是兩個駕著車的人,
總看著前方播映的,
卻沒有多花點時間看著彼此最耀眼的部分,
也沒有專心在乎彼此真正想要的是什麼。
朋友說中了,maybe we're meant to find each other.
因為我在這場夏季的狂熱中,
不斷的看到Deja vu,
老師說,那就是你生命中必然會發生的事情,
才會在無意識中已然看過。
我看著那個拾荒老人,心中忽然一片酸楚。
那晚,在陽明山的緊急燈光下,
其實我想說,
最初見面的那一刻,其實我們都對彼此嫌惡著,
你對於片肉不沾的我感到惱人,
我也對於那張撲克臉跟一副愛理不理的態度感到討厭,
倘若不是拾荒老人,
不是那包菸跟那罐茶的瘋狂,
我不會想再次共享一頓晚餐,也許我們就擦身而過。
而在那場作勢欲嘔的慌亂後隔天,
我在大馬路上大哭著。
也許當時就明白,接下來的路將存艱澀。
若當時毅然轉身離開,也許彼此都會只記得美好的部分。
冷氣團終於到了,
我想拋開一切狂熱,
回到最原本,簡約的生活。
沒有一大群朋友的熱絡,
但圍繞在我身邊的人,
卻總是能找來放心的聊些最深刻的心事。
我只想靜靜的當個書蟲,
在畫室不斷的畫畫,在剩餘有限的時間中向目標邁進,
我等待著一個能延續友情的apology,
卻遲遲未到。
才發現原來這麼簡單的一句話,
也必須如此漫長的等待。
我如此掙扎著是否按下刪除鍵,
即使明白按下了也不見得能回到原來的生活,
但至少,不能再讓心牽動。
如果我們真的有著最初的特殊緣分,
一定會再相遇的,不是嗎。
Goodbye then my dear friend...
Goodbye.
訂閱:
文章 (Atom)